汪曾祺的文学地位
时间:2021-08-31翻开当代的文学史,汪曾祺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为何会如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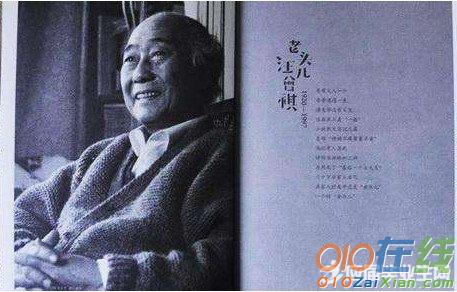
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
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
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 《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始状态中寻找人性的对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诱发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寻根小说的产生,对寻根文学“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启发意味。当然他们走得更远,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从钟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中,都可以寻找到一点汪曾祺的痕迹,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间”虽然是一个离开今天有一定距离的民间,但毕竟还是一个今人所熟悉的实体,而寻根作家寻得的民间却是已带有非本土特征的观念意义上的民间。
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派文学具有先导意义。“传统/现代”、“中/西”的冲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联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对现代小说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理论思考及大胆实践。
汪曾祺的现代性因素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他对传统语言观、小说叙事风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语言意识的作家,对新时期现代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是他的“语言游戏”和“近似随笔”的写法。汪曾祺极力主张打破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并将这种理念融汇到他的创作中去。汪曾祺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消解故事情节,强调小说氛围营造,推崇客观原则,以及作者与读者同构的美学观,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成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先锋人物。汪曾祺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将语言由工具论提升到本体论。如果说汪曾祺对小说语言文化性的探寻还只是实现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话,那么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次彻底性的颠覆。
作为这种颠覆的直接标志就是“先锋文学”的产生。马原被认为是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但新时期以来,将小说与游戏最先结合起来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新时期。虽然“先锋文学”主要受国外“横向移植”的影响,受汪曾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充当了先锋文学的肇始者和开山人,其给予“先锋文学”的点化和启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的“语言游戏”开辟了一个文学新时代。 汪曾祺强调“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我们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学的打通工作”,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沟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工作。他自己就是这种打通工作的倡导者、实践者。汪曾祺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坚持20世纪的文学应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但他不赞成中国有所谓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新时期一些小说家借鉴了“荒诞”、“新写实”、“实验”等观念而意欲完全摈弃传统,这不是明智之举。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标榜传统,也不无度地认同现代,主张应从世界获得文学先锋性的资源,但他强调这种吸纳如不在中国体验中找到结合点,就不能立足存活。
汪曾祺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他一再重申:“关于现代派,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办法使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全一样。”汪曾祺对先锋派文学革命的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认识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具有独创性,都无法脱离传统。传统总是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处。作家只有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能使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对传统的态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样持简单的否定方式,而是呼吁复兴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学。
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当代作家。和传统文化脱节,在他看来“是开国以后当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达默尔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他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人传统的“复活”与“转化”。“复活”是针对很长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传统的“断裂”而言的,“转化”则是指接受者赋予传统以“当代性”。汪曾祺是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对传统进行了跨时代的打通融汇和借鉴,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总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是经他丰富了内涵的新型的现实主义,新的民族传统,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现代主义小说理想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汪曾祺的现代小说理想是融汇了东西方美学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复出,新时期的文学才真正接通与40年代文学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人把他归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义。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京派作家为参照系,可发现现代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以及他融人自己艺术个性上的重构,大体有如下几点:其一,京派文学作品中凝结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思想,偏重于表现长期凝固在乡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强力和自然的质朴单纯,这在汪曾祺的新时期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此外,我们会发现汪曾祺与沈从文代表风格体现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特点。其三,京派作家使鲁迅开端的抒情写意小说文体走向一个新阶段,汪曾祺将西方文学中纪德、里尔克、阿索林等的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与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说进行融汇,他的小说趋向诗化和散文化,淡化情节结构,融汇传统绘画的技法,注意诗意的建构和意境的营造,把中国抒情小说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可以说,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这条审美线索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汪曾祺是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钟阿城、何立伟等,在创作上呼应着汪曾祺,使抒情小说在新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综上所述,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种影响又是不自觉的,正如他并不刻意追赶“现代”而具有现代意义。我们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可见庄子、归有光、契诃夫、阿索林、纪德、里尔克、伍尔夫、鲁迅、废名、沈从文等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影子,这使他的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与40年代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继承传统又打破了传统,进行了多元化重构,小说有这样写的吗?一时间争议纷起。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所以说,你根本无法用某一种定义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说,它就是它,无法复制,不可重述。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