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作品精选:额尔古纳河右岸
时间:2021-08-31引导语:《额尔古纳河右岸》,由迟子建所著,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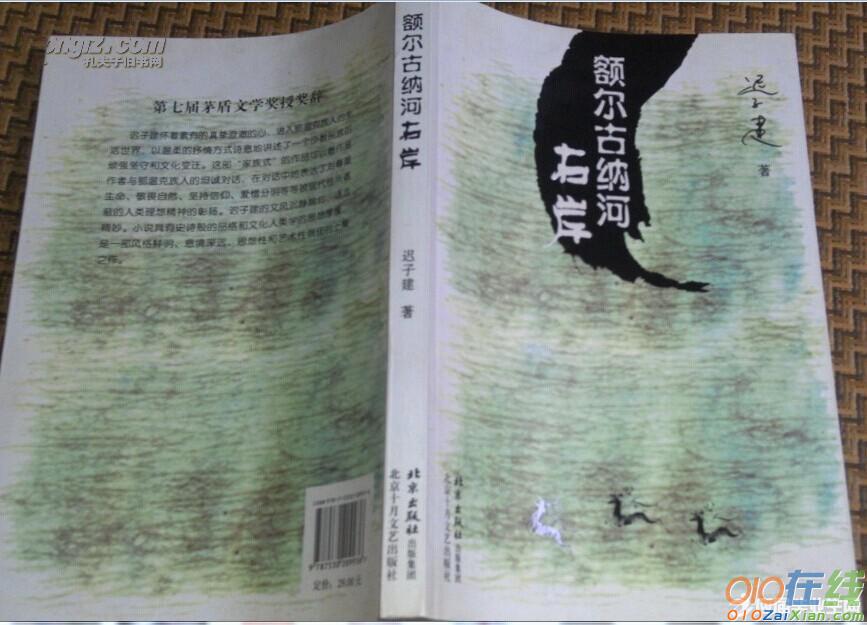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内容梗概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随机推荐
热门推荐
上一篇:迟子建:我说我
下一篇: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