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雨天作文
时间:2021-08-31积了一地雨水,已是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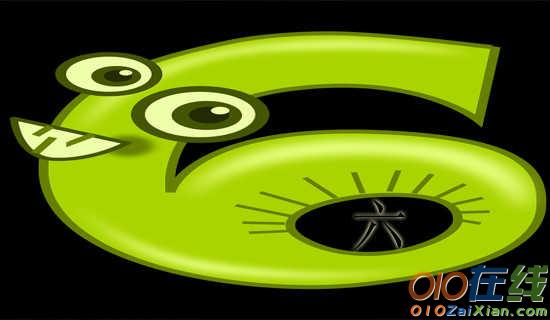
雷,在耳畔炸响。不知何时,雨点悄然落下。闷雷不住地在天穹回荡,从极远的天边传来,仿佛古时开战前的军鼓声。千百年前,我就知帝王一怒,那战鼓隆隆敲响,便是血染沙场的结局。那一声声“留不得壮士归不得家乡”的雷声,亦是人间的无数母亲唤儿归乡的悲鸣。那样的声音无法用笔墨描绘,只觉它似一曲独属六月沙场的挽歌,激昂又绵长。悠悠然,恍恍然,我便出了神,把自己忘在了这在我耳边振奋的雷鸣之中了。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风啸着,在窗外轻巧地玩弄着一株株弱柳,直至那树弓了腰微微地咳着,只觉平添几分萧索,却又似二十五弦弹清怨的潇湘妃子。风终是加快脚步绕过雨点,击在了教室的窗上。眼前是风,耳畔也是风,却仿佛眼前那斜了雨丝的才真正是雨中的风。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那风,却真是诗人的风了。
不再吟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抬头,看见了满眼浓浓的昏白。
真的,这窗外的那一端,什么东西如轻纱般的笼住了那景那楼那树。我不知它是什么。许是雾罢,春天它还是那样的扰人,转眼间便来得如此突然,阴沉沉的天更是染上了几分朦胧。
二月笼阳,六月笼雨,烟笼寒水月笼纱,也正是笼在了这几分朦胧。
雾越发地大了。远处的建筑已经看不见了,近处的朱红居民楼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
一抹幽然的朦胧被一窗斜斜的雨映衬着,似是一方雾琯雨结的深色丝帕,好看煞人。
我愿拥有那样一方精致的雨天。
我本想再看,然而同学的诵读声使我终是弃了窗外的雨。一盏茶的功夫,扭头再看,惊觉天已微亮,浓雾染上了些许微弱的日光。这轻纱般的幻象逐渐散去了,雨丝也越发细小,只余风声依旧萦绕耳畔。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不觉,天已大亮,建筑的轮廓重新清晰起来。阳光添了几分暖意,从窗外撒了进来。
不见太阳的踪迹,阳光也不大刺眼,只见蓝天依旧,白云千载共悠悠。浩瀚的天穹让我不禁想到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罢了,人类这样渺小,生活才是在天空下我惟一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