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作文范文
时间:2021-08-31小时候并不知道端午由何而起,我所关注的只是那香喷喷的粽子。后来,稍大些后,才知道端午是与屈原有关联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所感兴趣的并不是离骚与楚辞,似乎对于屈原的含恨投江也并不怎么关心,倒是觉得那么多白生生、香喷喷的粽子被白白地扔进了江里喂鱼而感到惋惜。总觉得纪念的方式有多种,譬如吹唢呐,大放悲声等,何必浪费那好吃的食物呢。这自然是一种很可笑的想法,从没好意思跟别人提起过,因为怕别人说我:就知道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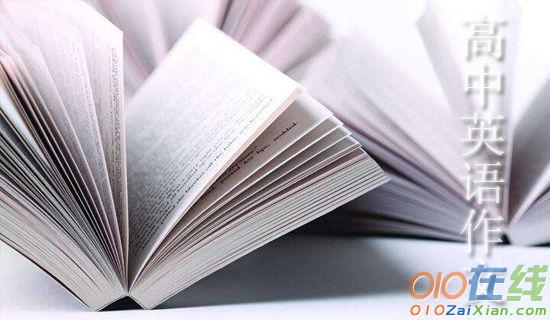
但“就知道吃!”似乎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需要有好吃的东西来填满我那干瘪的肚子,可是,每天除了高粱和玉米,不见油性的白菜外,其他的似乎没有。
年景好的时候,母亲会在端午的时候包些粽子。包粽子需要大米,糯米,黄米,还有红枣和红小豆,白小豆等,但这些东西都很稀罕,很难凑齐。
但到了端午的时候无论包不包粽子,我和哥哥与弟弟都要在上一年偷偷地去采些苇子叶来,也把院子里井台边的几蓬马莲适时地割了,捆成一把一把地,吊在房檐底下晾干备用。
那个时候苇子等都是公共财产,私人是不能随意动的。四十岁左右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保护公共财产而英勇负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人物。比如,有个小学生叫刘文学,为了保护生产队的几个辣椒,与偷辣椒的地主分子英勇搏斗,献出了幼小的生命。几个辣椒与一个稚嫩如花的生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似乎那样奉献非常伟大,非常光荣,那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是死得其所。
到了苇子长满池塘的时候,我们会冒了烈日去偷采些苇子叶。首先要装作拎着篮子去采野菜的模样,而且必须在中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那些恪尽职守的“看青的”才可能偷懒打个盹,使我们有“可乘之机”。
当然是由我或弟弟放哨,长我们几岁的哥哥飞快地钻进茂密的苇子塘里用最快的速度采些宽宽的苇子叶。遇到有人来,自然是学几声布谷叫,或咳嗽几声,这当然都是从电影里跟地下工作者学来的。
把采来的苇子叶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了一层野菜,以掩人耳目。说句实在话,为了吃几个粽子而冒这样的风险,实在有些不太值得。但是,食欲控制着我们,我们宁可去犯一回错误。
包粽子的苇子与马莲准备好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来年一定吃到粽子,因为要看这一年的收成如何。但收成是与天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个时候的天气似乎跟我们作对,不是旱,则是涝,风调雨顺的年景确乎并不多。
这一年,又到了快端午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看到邻居那个比较殷实的人家的小孩子已经拿着粽子在门口小口小口地夸张地吧唧着嘴吃了。我手里拿着玉米饼子,眼巴巴地看着那小伙伴手里的粽子,咽着口水。
“给我学一声小狗叫,我就给你半个粽子吃。”那孩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举着半个粽子对着我说。
“呸!我的玉米饼子比你的粽子好吃,谁稀罕!”我直着脖子,没什么底气地冲他喊了一句,扭头飞也似的跑回了家。进了门就喊:“妈妈!妈妈!我也要吃粽子!”
“吃你娘个脚!”没想到一向温和的母亲却瞪着眼冲我吼到。那个时候,母亲正在用筛子筛着一笸箩玉米面儿。
我“哇”的一声哭出来,跑着去找奶奶告状。疼爱孙子的奶奶立刻迈着小脚撵了过来,“孩子他妈,不做就不做,干吗那么吼孩子,看把他吓的。”一边说,一边爱怜地抚摩着我的头。
“娘,您不知道,又快断顿儿了,唉——”那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发出的一声无奈的叹息。
奶奶也跟着长长地叹了口气,“真是可怜孩子们了。”
奶奶拉着我去她的屋子里,从柜子里掏了半天,摸出一块焦黄的点心,送到我手里:“乖孩子,明年奶奶给你包好多好多粽子,好不好?乖,不哭,奶奶给点心吃。”说这话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奶奶那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又快到端午了,现在的孩子们恐怕没有谁能为吃到几个粽子而眼巴巴地翘首期盼了,也没有哪个父母因为不能给孩子做粽子吃而犯难了。现在的生活真是富足的很,温饱已经不是问题,并且许多人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但在这富足的生活里,我却总是在这五月暖风的吹拂中,在粽子飘香的季节里,想着童年时候吃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粽子,那么香,那么甜,那么让我难以忘怀。











